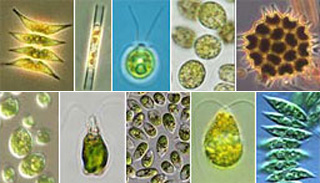一位癌症患者的看病经历:渴望一句温暖的话
点击: 时间:2014-04-11
近期,暴力伤医事件频频发生,引起了全社会对医患关系的思考。当前,医患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,但局部呈现紧张甚至恶化态势,主要原因是双方缺乏信任和理解。应该说,医患双方是一个战壕的战友,其共同的敌人是疾病。医患之间,只有真诚沟通,才能消除误解。为此,我们推出“医患面对面”连续报道,分别从患者和医生的视角解读医患关系,敬请关注。
——编者
一位癌症患者的看病经历
渴望一句 温暖的话
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 魏永刚
几年前,父亲得了消化道肿瘤。当父亲的病确诊之后,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,吃中药还是做手术?
中医和西医都能举出“正反”两个方面的例子,说明选择他们的重要性。如果真去看中医吃药,我害怕耽误了病情;如果直接去看西医做手术,又担心身体受到伤害。最后,父亲还是在医院里做了手术。
手术之后要出院了,父亲该如何疗养,我向手术大夫求教,他回答:没有特别讲究,和正常人一样。我特意问:是不是要看看中医,吃些中药?手术医生直接告诉我:吃中药没什么用。我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话,后来还是坚持让父亲吃中药,而且吃了好几年。
父亲最后住进医院,是因为消化功能减弱,进而营养不良,身体虚弱。检查结果是,肠胃蠕动缓慢,无法消化。医院除了输液补充微量元素,就是让吃西药增强肠胃动力。但一个星期治疗几乎没有什么进展。我问是不是找中医看看?医生说:中医也没有办法。
蹊跷的是,恰恰是中医有了办法。出院之后,我到家门口不远的一家中医院打听情况,医生说可以用针灸和按摩来试试。而结果是,第二天父亲就开始排便,效果让我惊奇不已。这样的经历,让我不能不信中医,又不能不听西医。
父亲之后在医院来来回回半年,我便往来于中医和西医之间。西医大都坚定地告诉我,不用看中医;而中医则流露出谨慎的不“自信”,却出其不意地总会有一些好结果。那些日子里,我最大的期盼是,要找到相信中医的西医,或者懂西医的中医,该多好啊!
随着父亲病情恶化,我急迫地拿着各种检查结果去找医生,得到的都是冷冰冰的回答:“没有治疗价值!”更有医生直接告诉我,这个病人最多能活多少多少天!
我反复向医生求证:不可能有“奇迹”吗?得到的大都是不耐烦的摇头。
我跑了北京五六家医院,到各种科室去排队咨询。护士温柔地问:你挂哪个科室?我常常反问她:我该挂哪个科室?几乎每次都得不到回答。每家医院都设立了问询台,但站在那里的人大多很年轻,他们从来不敢肯定地告诉你,可以去看哪个科,尤其是面对我这样想给一个被医生“宣判死刑”的人找“活路”的患者家属。
庆幸的是,不同的医生总能给出不同的回答。我最后还是找到一家医院,父亲得到了精心有效的治疗。我一直无法忘记那些决定“生死”的回答。也许,掌握了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真的能够看到病人的“生死”,甚至可以精确到几个月、多少天,但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,而且医学分工又是那么精细,从自己的角度看不到“活路”,难道别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吗?况且,生活中还有那么多奇迹呢。
医生要看病,也要给人信心。这是我在陪侍父亲的日子里,心里一直渴望却从未得到的东西。
父亲终至不治,离我而去。当我还在这不幸中难以自拔时,先后接到两个电话,这是我与医院打交道以来最温暖的记忆。
第一个电话是父亲丧事次日打来的。我正忙于繁琐的丧葬事务,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对方告诉我,他正是我父亲最后住的那家医院的医生。这位医生不是我父亲的主治大夫,仅仅是那个科室的大夫。他第二天上班之后才知道,患者在晚上没有抢救过来。于是,他到医务部门找到了住院时登记的电话,跟我联系。这位医生不无歉疚地对我说,当天下午下班时应该把手机号码留给我,那样在抢救的时候,我就可以联系他了。因为没有给我留号码,他没能告诉我抢救时该做什么。其实,他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我,但他那一番真诚的话,让我十分感动。我至今还一直留存着他的号码,尽管我再没有去过那所医院。
父亲去世快一个月的时候,我突然接到第二位医生的电话。他来自父亲以前接受介入治疗的医院。父亲在另外一家医院去世,我们没来得及再回到介入治疗的医院。电话里,医生很亲切地问候我父亲的情况,听到我的回答,对方沉默了一两秒,然后很缓和地说,他没有及时跟我联系,也没有再看到我们去复查,还以为病人正常呢。此时,这位医生才告诉我,父亲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,他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,是为了让我更有信心,也是为了鼓励病人。这位不善言辞的医生,让我感到无比温暖!
一位老年患者的就诊体验
将心比心 患者舒心
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李鲜华
俗话说:“树老根多,人老病多。”退休后,我频繁往来于各类医院。不久前的一次看病经历,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医患关系。
那天,我因患感冒到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洪山街社区服务中心看病。给我问诊的医生姓廖,一见面,她就很随和地说:
“您请坐,身体有什么不舒服?”
“咳嗽,嗓子里有痰,但是咳不出来,给我开点消炎药吧,我一咳嗽就会越来越严重,晚上不能平躺,影响睡眠,到最后不是打吊瓶就是住院,有一年还诱发了心电图改变。”
“好,你伸出舌头来我看看。嗯,你的湿气很重。”
“是的,我感觉身体非常沉重,尤其是下肢。”
“好,张开嘴,让我看看喉咙。你咳嗽是不是因为嗓子很痒?”
“是的,痒得忍不住要不停地咳,胸腹肌都很痛。”
“来,让我听听你的心肺。”听完后,廖医生告诉我:“你的肺部还好,呼吸道感染不严重,主要是湿气重,生痰,咽喉也有炎症,我给你开三天克林霉素,不仅仅是消炎,我们在临床上认为它对驱风湿的疗效比较好,你用了会感觉人轻松些。另外,我给你开两盒藿香正气软胶囊,你口服一个疗程,会逐渐改善湿气浊重的症状。至于咽喉痒,我给你开了金喉剑,这个药很好,我自己和家人都经常用,你用了就知道了。根据你的咳嗽症状,我给你开了杏苏止咳糖浆,回去按时服药,很快就会好的。这些都是最简单、最便宜的药,但是副作用很小,很安全,疗效也快,明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,你放心好了。”
听完廖医生的分析,我感觉医患双方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尤其是当她说“这个药很好,我自己和家人都经常用”时,我的心头顿时暖暖的。廖医生既充分倾听了患者的诉求,又理性发挥了医生的核心作用,成功建立了医患信任,让我愿意选择她,并将自己放心地交给她诊治。
我按廖医生的医嘱划价交费,总共花了51元。廖医生还亲自教我怎样喷金喉剑,在她的指导下,我当天就止住了咳嗽,三天后基本痊愈了。
廖医生带给我的这次愉悦的医疗体验,让我联想起此前赴大医院就诊的糟糕经历:挂号排队、就诊排队、划价排队、交费排队、检查排队、拿结果排队……似乎永远都有排不完的队,以至排队等候的时间累计起来是诊断时间的数倍乃至数十倍。好不容易坐到了医生面前,还没等我开口介绍病情,就被医生罗列的各种检查项目“分流”了,甚至很多用于检测重大疾病的非必要手段,也被作为常规检查方式普遍运用,由此产生的费用自然也是高昂的。这种完全依赖医疗设备排查而不体现医术价值的做法,很容易引起患者反感,也将医生置于潜在的危险境地。一旦在诊断环节仍然不能准确分析判断病情,很可能诱发医患冲突。当患者质疑有无必要做过多检查时,不少医生的回答竟然是:“反正有医保兜着,又不用花你的钱。”这样的结果不仅是浪费了医保资金,而且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。